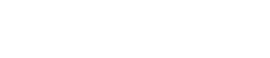我们往后追溯,20年后的上海,会是什么样的?这是很困难的。奈斯比特先生擅长从普通的报纸、别人看完了就扔的资料中发现未来的十年和二十年。如果我们要求他知道未来30年,就太刻薄了。没有人能预言得那么远。奈斯比特先生和多丽丝常到中国来。他最熟悉的,是北京、天津,他在天津成立了研究所,天津的两个大学和他合作。刚才焦扬女士说,你跟奈斯比特夫妇提个要求,在上海多住几天,研究一下上海。以往邓小平先生每年到冬天就到上海来,日本的记者在日本问我,为什么邓小平先生每年到上海去?我回答,一,冬天北京太冷,上海的气侯他习惯了,他的饮食也习惯,可以使他的健康得到保证,二,上海是研究中国经济最好的地方,他在北京研究中国政治,到上海研究中国经济。所以,每年他到上海来。日本人按照他们的习惯回答,“明白了”。第二天,见了报纸。我这是讲给约翰和多丽丝的。你们很钦佩邓小平,要步着邓小平的脚步研究上海。他们微笑了,就表示同意了。
20年后的上海什么样?我们可以有不太离谱的上海梦和中国梦。有些梦,今天看来很离谱,但实际上没有离谱。最生动的例子,就是100年前,上海有一个叫陆士谔的人写了一本小说,《新中国》,他 一百年后会在上海浦东举行世博会,会有跨江的隧道,浦东和浦西一样繁荣,道路宽阔、车马往来不绝,电灯到处点亮。今天我们实现了这位陆先生的梦。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事情。所以,如果没有想象力,就没有好的明天。
20年后,上海和纽约、伦敦、巴黎、东京相比,也算一个可以并列的城市了。中国的人均GDP应该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了。中国必然是能为世界做较多的国家之一。这不只是中国,还有印度、巴西,还有南非,也许还有俄罗斯。都是这样的。中国并不想自己一个国家前进,一定要大家一起前进,才能和谐和和平。
20年后,中国的文化呢?我们大楼、工厂没有落后。我们的文化,怎么样呢?归纳文化问题,很难用数字。但我们也不能不想象一下。中国近几百年以来,英国的里约斯特说,近百年来,中国对世界的科学贡献比较少,今天我们说,我们是文化大国,其实,我们是在分享祖先的光荣。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,我们是愧对祖先的。在1895年以前,日本每年翻译中国书200本。1895年以后日本人每年满意中国的书2本。那就是中国文化没落的象征。
文化的最主要载体,是图书。我们今天中国图书版权对外贸易存在着严重的逆差。在经济上,如果有20%、30%的逆差就很严重了。但文化版权的贸易,中国是500%的逆差。中国卖一本版权,要买外国5本。这还是平均的说。对欧美,我们买他们100本,他们才买我们一本。这很令我们着急。但也不能简单的说,这是外国文化渗透到中国来了。因为我们翻译的书,特别是欧美的书,大量的是高科技书。不能想象美国人翻一本中国的生物工程,或者美国人翻译一本中国的IT技术。没有的。一定是我们翻译他们的。我们出口的书,一些还是古典的。如《三国演义》。我们的《本草纲目》在亚洲文化圈内,也能出口, 中国的食谱也能出口。外国人学汉语的教材书,出口很多。但小说就较少。所以我们中国接纳世界文化的时候,要想到我们要回馈世界。如果不能回馈,那我们心中就是一种歉疚。
上海人被人公认“海纳百川、有容乃大”,今年又提升为“海纳百川、追求卓越、开明睿智、大气谦和”。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。如果这个标准能在上海植根,上海就不再只是一个经济大城市了。我们就能更好的服务全国、贡献世界。
我们在仔细阅读中国、阅读上海之后,我们要明白,我们处在一个空前的伟大的变革时代,我们自己要敏感。多丽丝说,中国在变化中。而我们,在中国列车上,是逐步加速的,我们自己没有感觉,好象是平常的日子,其实不是。
伟大的变革时代,应当诞生伟大的作品。伟大的作品,应当描写时代的文化变迁。伟大的作品,应该有横向的向世界传播的力量。伟大的作品,在纵向,能够有遗传的潜质。否则这个作品只印一次,不是最好的作品。
时代是作家之母。大作家是佳作之母。我们需要能真切体验现实生活的伟大作家,写世界意义的作品的作家,需要保持与世界文化的沟通。刚才约翰•奈斯比特先生阐述了《中国大趋势》的主题,提出了支持中国发展的八大支柱。这些支柱,就在我们身旁存在并且长大。但我们没有把它们归纳出来。这对我们,不就是一种启示吗?